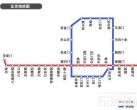儿时的敬胜胡同
上个月的一天,我带着儿时的憧憬,带着思念,凭着记忆,走进砖塔胡同,拐进了敬胜胡同,一边走还一边画下了路线图,生怕漏下点什么。我看着这一个个院门,想起了一件件的往事,说起来都是我儿时八岁前后的事了。
在敬胜胡同一进口的对面是砖塔胡同的北面,这儿有一个大杂院,现在看不见这个门了,每当我父亲带我出门经过这儿时,看见停在门口的三轮车,就让我进去叫出车夫老张,他车上的托泥板总是锃光瓦亮的,那辆耀眼的三轮车让我记到如今。在这个大杂院的西边有个小门,现在也不见了。早先,进了门的右边是一间诊室,有一天我的耳朵疼得睡不着觉,我二叔说:“别哭,我给你买串糖葫芦吃就不疼了。”可是一清早我父亲就带我上了这个诊所,一个外国男大夫看了我的耳朵后,用一根长棉签在我的耳朵里出出进进,说是洗耳朵,说我的耳朵里化脓了,要天天来洗。
进了敬胜胡同路东的第一个门,现在是二号,原来这个院里有一家绱鞋的,那时我们都来这儿绱鞋。绱鞋的师傅住在院内左边的一间小西屋,他面朝门,坐在一个高凳上,眼前有一个矮桌子,两腿夹着两个木板,木板间夹着一只鞋底,还连着一只鞋帮,手里拿着一根大针和一个锥子,不时地往鞋底儿扎眼、穿针、拉线。每当我去送鞋,他只是抬一下头说:“就放在那儿吧。”这个场景就像一幅画,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说到鞋,我的继母每年都给我做两双,一双是一字带的单鞋,一双是骆驼鞍的棉鞋,从打浆子、打袼褙、剪鞋底、剪鞋帮、剪沿条、粘沿边、粘底子,到搓麻绳、纳底子、做鞋帮,这一系列的工序,我何止看过一两遍。当我成家后生活困难时,我也能为自己、为孩子们做双鞋穿。妈妈教会我不少生存的能力,使我今天才有了持家过日子的本事。我很是感激她也很想念她,可是自从分别后至今也没打听到她的地址。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记到如今,就是这二号院经常敞开的大门。那年我在普化小学上五年级,当了班长的我更是爱管闲事,班上有两个男生总是吓唬女生,一次竟把一个女生吓唬得哇哇大哭,我告诉了老师,老师惩罚了他们。第二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他俩总跟在我后面,我忽然想到不能让他们认识我的家,当我进了砖塔胡同后,赶紧拐进了敬胜胡同,一溜烟就钻进了二号院,藏在了大门后面,藏了好半天没发现他们过来,我才出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沾沾自喜,庆幸自己骗过了他们。进了敬胜胡同一直朝前走,到头拐弯往西,在不远的左边有个窄胡同叫小院胡同,现在还有这个胡同。我父亲常带我穿过这条小胡同去大院胡同孙大爷家,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和孙大爷以及孙大爷的弟弟在民国时期都曾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手下任要职。后来堂兄来我们家住,我们也常从这条胡同穿过,走出大院胡同,在缸瓦市车站坐上有轨电车,到司法部街小学上学。一天,有一条小黄狗跟在我们后面到了家,进了屋它就蹲在地上不走了,从此我们收留了它。我让哥哥给它起个名字,哥哥说就叫它“小黄”。从这以后,我们家的剩饭菜就成了小黄的美味佳肴。它没有窝,随意卧地入睡,早上我们去上学,它就跟在我们后面,一直看着我们上了车,它才扭头往回走。下午我们放学了,它好像心里有个钟点似的,时常看见它在大院胡同的口上等着我们。如今看见黄色的小狗,就不由得想念起我们曾经收养过的小黄。
顺着南墙一直往西走,有个高台阶的大红门现在还在,它的西边是个没有台阶的小红门不见了。再往西一点,路北有个豁口呈凹字形,里面有三个门,坐东朝西的16号就是我们家原来住的8号院,我们住的南屋的临街三个后窗户依然存在。中间的17号坐南朝北是原来的甲8号,坐西朝东的19号是原来的9号。看见当初我们家的这三扇后窗户感到特别亲切,是它让我自幼就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多彩,享受到民间美食的口福。那时我经常在第一时间听到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在这里我看见了耍猴的,吹糖人的,捏面人的,还看了皮影戏和懂得了已碎成两半的碗是如何锔上的等等。我还吃到了许多好吃的,就说那“半空儿”,提起它来没有不想的,甭提多香,越吃越爱吃,直到吃光才罢休。我正在东张西望时,从15号门走出一位住户,与他交谈中提到原来的木头门,现在已经换成铁的了,但那门坎我看得出来还是当年的那块又高又厚的木头,只是残缺得太多了。
这个院子更是让我抹不去对大哥的思念,这儿竟成了我和大哥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大哥是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生,抗战后派到南口执行公务,时任营长,后来听说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后来他随军去了台湾。那是1948年的一天,大哥来家里辞行,想到那天的情景,就如同在眼前,那天早晨,大哥站在外屋八仙桌的西边,爸爸穿着深色的大褂,忧郁地走出了东屋,可以看出他对儿子的担心和无助。我瞪着圆圆的大眼睛,不解地望着高高个子的大哥和爸爸,叫了一声大哥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远走的大哥始终让家人牵挂,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封闭了几十年,毫无音讯,改革开放后,几经周折,两岸终于能够往来信件了,在朋友的帮助下,了解到大哥的情况,可是大哥已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失语,住进荣军医院多年,后于1992年病逝。自从小院一别,我再也没能见到远隔海峡的孤独的大哥,这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当初的9号曾经住过日本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们搬走了,我姑姑家搬来了。他们门口南墙角比我家的南墙角长出一点,有一年春节,淘气的堂兄把一个二踢脚炮仗插进了墙角边的墙缝里,点着后炮仗横着就蹿了出去,吓得我扭头就往家跑,正和出门的父亲撞了个满怀,我父亲猜到又是哥哥的恶作剧,结果他又挨了一顿揍。今天这块墙砖还在,只是风化得太厉害了,哥哥你走的太突然了,要是能等到今天,我一定在这儿留个影寄给你。我家南屋后窗户的对面是敬胜胡同的南墙,这儿的电线杆子还在,只是换成了水泥的。向胡同的西头走不了几步就往南拐了,现在叫三栅栏北巷,小时候常穿过这里去油盐店买盐、打醋,就在三栅栏北巷入口的东墙角上,有个高台阶的大红门总是关着,每当我经过这儿时不由得冒出一个想法:这个大门里不知是什么样儿?这次来到这儿,没有看见这个大红门。在入口的对面是西边,也有一个电线杆子还在,也是换成水泥的了。我上五年级的时候,趁姑姑不在家,我就搬出了她的自行车,没练几天我竟能坐上骑了,一天我想骑车拐进三栅栏北巷,结果直奔了这根电线杆子,把自行车的前托泥板给撞掉了,我自己倒是哪儿也没碰着,怕挨呲儿,从那以后再也没敢骑车玩。这里是敬胜胡同的尽西头,那时候再往西没什么住家了,如今这里却是高楼耸立。我往回走,东头的胡同两边停放着不少车,数小汽车最多。我请出来晒衣服的住户为我留影,他们都非常热情,有挪车的,有挪衣服的,为我留下了今天还能看到的儿时旧景,真是宝贵难得,我想,过不了多久,敬胜胡同就会旧貌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