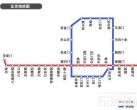北京城的传说之水窝子和四眼井
2012年05月06日
自古以来,老北京平原地区是个以砂砾石沉积为主的洪积扇平原 ,开始是沼泽地,湖泊河流很多,因为水皮很浅,所以水井大多是苦水,只有较深的水井是甜水,
元大都建城时,以水井为中心形成棋盘式的城市布局。人们围井而居,逐渐形成胡同的居住模式。有句老话: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就有多少口水井。可见北京的水井多得无法统计。据说“胡同”一词即为蒙语“水井”的译音。
而占有甜水井的井主,往往不让邻居们自汲,而是招人给送,以此赚钱。这样老北京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生意——“井窝子”,即卖水的水铺。 
北京城外的水窝子,后面是北京的城墙。旁边是水箱和送水的水车。(1901)

北京城里靠近皇城的水窝子,后面是东安门。,右面是皇城根。(1932)

井窝子的掌柜,往往由把持一口井,发展为把持一条水道。老北京的东西南北城,分为若干条水道,每一水道都有一掌柜经营,指挥水夫,向本水道内的住户和店铺送水,掌柜称水夫为伙计。
那时,井窝子的生意很兴隆。这是因为北京的井虽多,但不少井水发苦,无法食用,就连漂洗衣服都不好。因此,皇宫每日都派人用车从玉泉山运泉水,而不少居民也不得不舍近求远,到甜水井买甜水。买甜水,当然不是指提个桶去买,而是由井窝子的水夫送到家中,倒进缸里。所以清朝得硕亭《草珠一串》中有一首竹枝词写道:“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著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

北京城外的水窝子,后面是北京的城墙。旁边是水箱和送水的水车。(1901)

北京城里靠近皇城的水窝子,后面是东安门。,右面是皇城根。(1932)

井窝子的掌柜,往往由把持一口井,发展为把持一条水道。老北京的东西南北城,分为若干条水道,每一水道都有一掌柜经营,指挥水夫,向本水道内的住户和店铺送水,掌柜称水夫为伙计。

每天清晨六七点钟,水夫们就推着水车,按路线把水送到主顾家。到了主顾家门口,水夫放下车子,拿起扁担,用扁担的铁钩子,将两个小水桶分别钩放在大木桶两边,一拔塞头,水即流出,两桶一起装满,塞好塞头,将水挑到主顾的厨房,倒进缸中。


水夫们多为山东人,他们坦率诚实,挑水进门,目不旁视,不论多热的天,不打赤膊。统称“老三哥”。

钟楼下的水夫
水夫们记账的方法极为有趣,他们用尖利的小石块,在主顾家门旁的砖墙上画若干道的印儿,别人瞧着,一点也不懂,而他们自己却是一目了然。

20世纪30年代以后,自来水逐渐普及,井窝子的生意日趋冷落,直至最后消失,“水伕”这一职业也成为北京的历史往事。

消失的职业---水夫

北京的四眼井(拍摄于1929年)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曾随姑姑住过大佛寺,前门外施家胡同,阜外四眼井胡同。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胡同叫四眼井,(那时早有自来水了,北京的井基本都填了,据说后来四眼井胡同改成阜外头条了),后来看了这张老照片,才知道老四眼井是这个样子的。
据说,这口井还有故事呢。
老北京人都知道清皇宫的御用水均来自西郊的玉泉山,拉水的水车进出城都要经过西直门。每当黎明时分,住在西直门大街两侧的老百姓,就会听到马拉木轮水车的“咕隆”声和随之而来城门开启的“吱扭”声,不用说,这又是皇宫水车出城去玉泉山拉水去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总是如此。
据说,这口井还有故事呢。
原来,那个押运水车的老差役,快进城的时候,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头,赶快停下车,向水车上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原来路上颠簸,出水口没塞好,一车水流光了大半。老差役心想,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本来自己就喝高了,已经误了时辰,现在水又漏掉不少,这可如何是好。如果再返回玉泉山,时间肯定不够。酒壮怂人胆,老差役借着酒劲急中生智,听说阜成门外有个甜水井,就悄悄地来到阜成门,当时还没有名字的一口水井前,急急忙忙地补满了一水车,再回西直门,所以回来晚了,进了城门,慌慌张张地押着水车赶向皇宫,提心吊胆地交了当天的差。没想到,慈禧太后喝了这假冒的玉泉山水,没发现异常,觉得与往日玉泉山的水一样甘甜可口。自打这以后,老差役的胆子越来越大,每次进城前,都要停下车来看一看,洒多少就用这口井的水补多少。时间一长,慈禧太后喝此井水的传闻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里的人都来这里打水,全想亲口尝尝慈禧太后喝过的水。

还有一个传说,说是一个地主家有四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为了争夺家业,吵闹不休,特别是为了一口甜水井,这是一口宝井,不但井水充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井水是甜的,泡茶好喝,做饭饭香,做鱼味鲜,做肉肉烂。说是长喝这井内的水,还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因此兄弟四人暗暗拿定主意:地可以少分,钱可以少要,就是这口井非要不可,互不相让,争执不下,最后地主灵机一动,萌发一念,把井分为四份,这样免得儿子们争吵,可是咋分呢?想来想去,想去了一个妙法,让石匠弄了一块大石板,做一个盖,凿上四个眼,这样一人一个井眼,各用各的井眼,各吃各的水,免除了兄弟四人的争执,顺利地分了家。就这样传下来这口四眼井。
无论什么故事,从照片看这口井,从四个井眼边缘被井绳磨出的一道道深沟上,可以想象出当年方圆几里的人们争打井水的热闹场面。
无论什么故事,从照片看这口井,从四个井眼边缘被井绳磨出的一道道深沟上,可以想象出当年方圆几里的人们争打井水的热闹场面。
有人考证,阜成门外的这口“四眼井”是当初修筑明城墙时为了取水方便而挖的,可见“四眼井”确实是一口年代久远又有着传奇色彩的古井。
我在网上随意的搜了一下四眼井,却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四眼井,看来中国的文化还是很相通的。

青岛的四眼井,井已经封了。

浙江诸暨的四眼井,据说西施用过。

安徽安庆的四眼井,看来利用率挺高。

台湾澎湖马公岛的四眼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