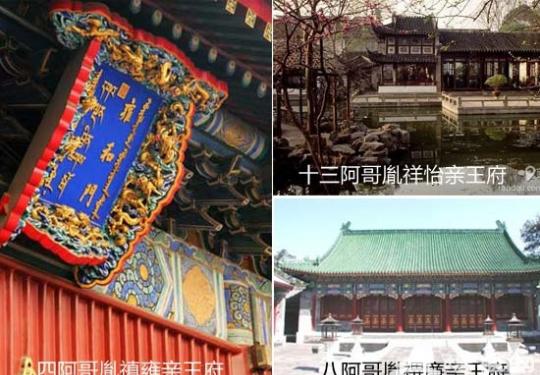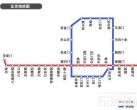京城的王公府第
2012年03月08日
五.京城王府的实地勘察
本人多年来痴迷京城文化,闲暇时时常徜徉于京城的街巷胡同之中,感受京城厚重的人文气息,捕捉行将消逝的旧城影像。在翻阅了许多有关京城的文献资料后,深感王府在清代和近代京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小说(如曹雪芹《红楼梦》)传记中的很多人物都与王公府第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最著名的两部杂记—奕赓著《佳蒙轩丛著》和昭梿著《啸亭杂录》均出自王府;慈禧和恭亲王奕訢策动“祺祥政变”,将三位显赫王爷载垣(怡亲王)、端华(郑亲王)、肃顺(辅国将军,御前大臣)致死并没收了他们的府邸。流传至今许多文化、习俗也出自王府,如:蒙古车王府收藏的曲本;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书法绘画大家允禧、永瑆、永瑢等。饮食中有“满汉全席”;定王府的“砂锅居白肉”;庆王府的“茯苓饼”等。近代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也与王府“有缘”,譬如:庚子事变中有六座王府(端郡王府、质亲王府、庄王府、肃王府、履亲王府、诚贝勒府、)被焚毁,同时还有几座王府(礼王府、、直郡王府、朗贝勒府、贝勒永璂府、橚贝子府等)遭到抢劫和损坏;从1860年《北京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先后有四座王府被辟为使馆(英国使馆—梁公府;法国使馆—纯公府;日本使馆—肃王府;奥地利使馆--裕王府)。还有几座府邸被外国势力攫取利用,如:恭王府和涛贝勒府被教会用借高利贷方式收购,兴办辅仁大学;豫王府被美国油料大王洛克菲勒收购,兴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当初就保存在那里,运出后至今下落不明。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我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最初就选址于沙滩后街的和嘉公主府。民国时期,和亲王府成为段祺瑞执政府,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那里。时常路过一些街巷,看到路边的高大的青砖围墙,仰头可见墙内镶以吻兽的琉璃瓦顶;偶尔从某座楼顶俯视可见一大片豪华轩敞、错落有致的殿堂,经打听得知是某某王府。这样的经历一多,逐萌生了探求的愿望。翻开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可以看到除了宫苑、衙署、仓库外,最明显的标记就是王府,竟有37处,另有四处由王府改成的寺庙(贤良寺、雍和宫、玛噶喇庙、光禄寺),还有一座由王府改成的昭忠祠(原安郡王府)。可以说,王府称得上是清代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乾隆朝之后又兴建了许多新府(如醇王南北府、恭王府、庆王府、理亲王、循郡王府、涛贝勒府、洵贝勒府等),王府的数目应是相当可观的了。但从民国三十六年(1947)京城地图上看,许多府址已从
地图上消失,剩下的除个别原府址外,大部分府址已改变了名称,冠名最多的是学校,其次是医院、官署等。时代巨变,孕育了厚重的人文历史,也如同一道高大的府墙把我隔在时代沧桑之外,让我无从想象其中的缘由,却引发了我踏查神秘府邸的愿望。
1.孚郡王府(九爷府)
记得是在1999年4月的一个周末,这一天成了我大规模踏查清代王公府第的开端。按照书中所指的孚郡王府(九爷府)的位置,我一大早赶到朝内北小街南口,没费工夫就找到了一处旧式临街大门,两旁竟挂着十几个单位牌匾,几位附近的住户正坐在门外,享受着春季的温暖阳光。门中间仅剩两排红漆立柱的通道勉强可使汽车通过,但柱面上已留下了许多被车辆擦蹭的痕迹。一进院子,一座宽阔高大的屋宇式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分踞两旁的高大石狮透射出一股威严,从没见过的这般景象,不禁让我在大门前的空场上驻足端详了许久……。走上台阶,用力推开两扇镶满金黄色门钉的大木门,抬头遥望,一圈突兀而起的殿堂像一座庞然大物罩住了我的视线。面阔七间、带斗拱和彩绘的绿色歇山琉璃瓦顶大殿(银安殿)坐落在由汉白玉砌成的高台阶上,前列丹墀,大门与大殿之间相距近四十米,由石基甬道相贯通。正殿左右各有一座面阔七间的配楼,两座配楼之间的距离比甬道还略长一些。大殿两侧有配楼,和大门一起由精致的庑房和转角屋连成一体,形成一座豪华宏阔的院落,既威严壮观又紧凑舒展。这种规格的宅邸,让我始料未及,我由此联想到故宫的太和殿,这两座殿堂都是举行礼仪之所,虽然二者仍相差甚远,但这种府第的建置规模绝非一般官邸和私宅所能相比。照看府门的先生出于善意,让我能仔细观看,他也不时地给我讲一些该府的逸闻趣事,令我耳目一新。
当我试图从大殿后面再往里面走,却被大殿两旁砌起的砖墙阻挡,要进到后院,只得从外面绕过去。向看门的先生道了谢,我穿过府门外的东侧门(东阿司门)就往里走,所经过的路段应该是原府的东路部分,水泥路两旁裸露出一道与府门侧墙相连的断墙头儿,显然是为这段路而豁开的。一处有叠石残迹的基座上竟盖了一间红砖房,我想象这里以前应是一座亭子。除了可以辨认出的几间旧房、几棵古树以及被堵死的连通中路部分的侧门外,东路部分已完全被杂乱的违章建筑和住所分隔挤占,看不出府邸的样子。进入王府大殿后面(后寝)的通道就设在东路最里边,一道闭合的铁栅栏门上只开了一个小转角门,这显然和大殿那里不是一个单位。在进门前我有些犹豫,想了想就壮着胆子往院子里走。真碰巧,看门的人正坐在门房里埋头看报纸,没有理会我,让我暗自庆幸。踏上一个高台阶走进后院,只见绿色的殿堂周围花木扶疏,格外宁静。 这又是一座高大厚实、做工考究的四合院落,与正门、大殿均在一条由南向北轴线上,院子的宽度比前院略窄,近深也短一些。主配殿前佩着雀替并带须弥座的红漆廊柱和檐廊两侧雕饰精美的仙鹤图案,在斜射的光线映照下十分夺目。后寝正殿也面阔七间,如同寺庙殿堂一般宏伟,有高出地面的汉白玉殿基和丹墀,殿墙侧面镶嵌着绿琉璃图案,脊顶两端配饰着吻兽,檐角上排列着玲珑剔透的怪兽。院中的花木正直盛开季节,散发着春天的气息。两棵高大的古槐占据在矮树丛围成的大花池两端,繁茂的枝杈遮住天空,投下一片浓密错乱的光影。按习惯讲,老宅的内院不种这样的大树,但像王府内这样宽敞的院落,如此装点到来得恰好。花池的东西两侧还各搭了一个藤萝架,虽非府的原物,也使整个院落更显古朴凝重、静谧安闲。在院子的每个角落,都能品味到不同的景致和建筑细节。寝殿两侧各辟出一个小跨院,里面厅廊错落、花木掩映,显得深邃幽远,另有天地。和府邸的前院相比,这后寝院更有怡神养性的味道。这里也被几家单位占用,两侧的房屋还住着一些人家,依然有一些搭建的违章建筑。顺着后寝和跨院间的一条过道进入到最后一进院子,一座面阔七间的高大后罩楼背靠着府墙,成为整个中轴线上最后的标志建筑,后罩楼的两侧各有一排房屋向两边延伸并折转,勾出了后院的轮廓。罩楼正面上下的檐廊已被封住,和房间一起当作了图书馆和部分住家,前面的空地上竟开辟出了一个围有铁丝护网的篮球场。
后寝与前院银安殿后侧之间是一块由条石铺就的近一米高的狭长平台,形成了一个从前院到后寝的过渡带,我起先没能从前院走到这里。坐落在平台北端的一排高低错落的厅堂应是进入后寝的宫门,现也用作了办公场所。在平台两侧的下方,各有一块空地,背靠着宫门和庑房,地上铺有方砖,每块空地的一角栽有一棵枝干紧簇的老海棠树,西侧的海棠树旁摆着一圈做工讲究的桌椅,使这块不大的地方更显出几分清闲。银安殿后墙檐下堆放着几尊褪了色的近人高的木质“四大天王”造像,姿态生动各异;后墙上还涂有依稀可辨的“大办民兵师”的墨迹;房顶上、砖墙缝间和墙根透风旁结了许多枯草。由于是周末,四下里静谧无声,见到这般落寞的景象,心里顿生了几分恐惧。这些从未见过的景观,让我手持着相机忙个不停。由于紧张又怕被管事的人发现并逐出而失去机会,动作也有些忙乱,连更换胶卷和镜头也觉得耽误事儿,竟急出一脑门儿的汗。
府的西路部分比中路建筑明显矮一些,屋顶一水儿的青灰色筒瓦。这里应是原府上家眷的住所,由多组院落组成,与中路之间仍被一道高墙隔开。除大门西侧的西阿司门外,此墙上也有一道被堵死的通道门与中路相通,可以想象当时的王爷抄近道就可进入内宅,而不必惊扰更多的人。这里现已完全成了居住区,老房四周到处充塞着私搭乱建的房屋,形成了一条条狭窄曲折的过道,使人感到局促。顺着过道往里走,就像进入了一座迷宫。除了能看见一些被严密裹住的老房和游廊残迹外,让人无法辨认这里的整体格局。换上超广角镜头,也很难将所看到的旧府景物拍得完整。从能看到的那些磨砖对缝的青砖墙面、精美的戗檐砖雕、精巧厚实的房屋举架、依稀可辨的彩绘、房脊上细腻的砖雕图案等等,也足以揭示出这座王府昔日的建筑规格和主人的显赫地位。
整座府邸现今仍围有一圈厚实的府墙,有4米多高,由大块灰色城砖砌成,墙面已显斑驳。府的纵深从朝内大街向北一直甩到了东四三条,近二百米。从三条东口沿着后府墙从东向西,走了近三百六十米(共跨七根电线杆有余)后,看到府墙又折向南边。粗略估算,这座王府原先占地有百余亩。初次踏察,虽属走马观花,却使我对王府有了一个实地印象:王府之壮阔体现出权势的威严,其深邃精美的院落和园林又有更多居家享乐的氛围。王府的建置规模介于故宫和官邸大宅之间,主路建筑(核心建筑)坐落在一条南北向纵深的轴线上呈对称状,两侧辅与大型附属院落和花园,并围以高大的府墙是其建筑的一个特色。如果把王府和故宫做个比较,王府大门和正殿相当于故宫午门、三大殿到乾清门之前的部分,即外朝;王府的宫门(后寝门)就相当于故宫的乾清门;从宫门到后罩房之间相当于故宫乾清门之后的部分,即后寝;王府中路两侧的附属建筑也和故宫中路两侧相当。当然,这只能是类比,清代王府的建造多少要受到皇宫建筑的影响,但也有满族贵族自身的特色。王府形制虽不像故宫那样浩繁,但也体现出封建皇权的至尊。
在此之后,我又多次踏查过该府,是为了拍出更多满意的照片,其中有两次经历令我至今难忘。一次是在第一次踏查后不久,我碰巧转到府墙西侧的一个即将落成的现代别墅住宅小区。为了能观看到王府西路的格局,我混入民工队伍进了院,走到紧靠府墙的一座别墅楼的二层平台,发现还是有些遮挡。要想看得更清楚,只能爬到楼顶,且有危险。我犹豫片刻,随后将相机跨在胸前,恳求两位民工将我托上瓦檐,小心翼翼地爬到了小楼的顶部。高度虽不理想,但可看到王府宅邸浑厚舒畅的轮廓从一片低矮杂乱的建筑物中清晰地显露出来。拍了照后我就立刻往下撤,感到心脏砰砰直跳。从放大的照片上,我看到整个西路也呈严整对称的格局,由多个四合院落组合而成,紧贴府墙,有一条长长的后罩房横跨整个西路后部,前面还有带悬山式屋顶的殿堂,仅整个西路部分就相当于一所豪华深宅。后来一.想,那座别墅已住进人,再也没机会如此拍照,真感叹那次难得的机会。
为了从高处能拍到俯视王府的全景,我不只一次地试图登上位于府西侧的一座商务楼顶,这也是府旁唯一的高处,结果不是被楼顶上带锁的铁门阻挡,就是因没有“充分理由”而被守门的门卫拒绝。一个雪后的下午,我和一个朋友驱车正要经过该府,出于想再试试运气,也因有哥们在胆子壮些,我停住车,和朋友一起蒙过了门卫,直奔那楼顶而去。当看到那道铁门正好打开着,门旁摆放着刚扫过雪的笤帚,我顿时喜出望外,赶忙来到楼顶一侧,掏出相机一通狂拍。雪后的天空清爽透彻,王府的绿色琉璃瓦顶仍挂着残雪,衬着瓦蓝的天空,在冬日的阳光照射下,雍容华贵。和远处高耸错乱的楼群相比,鳞次榤比的绿色殿堂看上去浑然一体、极具韵致,如同一颗夺目的宝石镶嵌在悠悠古都之中。当时天气寒冷且刮着大风,朋友已冻得得难以忍受,不时提醒我赶快收场。而我却忘记了寒冷,按各种景别构图拍个没完,生怕漏掉好镜头,一直挺到尽兴为止。后来每当回想起这次经历,总有一种难以形容快慰。
我现在已无法记清我去孚郡王府的次数了,可以说有好几十次了(有时是陪朋友)。后来心态放松了,每逢到此,总能找到新的视角拍摄,也会有新的认知和感受。为了拍出一张完整的府门照片,有多少次看着门前停放的车辆而无奈。一天下午,光线正好,门前只停了一辆车,我等了一阵,看到那车的司机走了过来,我以为他要驾车离开,没想到他是来收拾车子。我凑过去好声相求,还真给面儿!他随即把车开到一边腾出了空儿,让我终于如愿以偿。还有一次在大门前,我因系鞋带而弯腰,摄影包内的莱卡镜头随即滚出掉到地上,看到后尾镜片被摔裂,当时无比心疼和懊丧!由于这支35毫米主力镜头缺阵,我也只好“歇菜”了一段时间,当时也没心思再“出击”了。维修这种镜头须经香港再转到德国本土,三个多月后才修好,维修费竟要了5000元。这也算是一次不幸的经历吧。
其实京城里比这处王府完好的景点多了去了,不说故宫、北海、天坛、雍和宫等等,就拿各处开放的寺庙、衙署甚至恭亲王、醇亲王府花园来说,虽都修复一新,招引着游客,但过分的添加景观和游览氛围已使这些古迹失去了原有的神韵。像孚郡王府这座“饱览沧桑”的旧邸,却让人有走进历史隧道、独赏悠悠古韵的情致。
2.令人惊叹的履亲王府遗存
根据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所标的位置,东城区东北角的针线胡同(旧时称旗杆胡同)曾有履亲王府和贝勒允祁府。有关文献上记载:“咸丰时,履亲王府着了一场大火,王府被烧毁,变成一片荒烟蔓草……”实际上,履亲王府遭受火灾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庚子事变有关。当时义和团烧毁了与王府相邻的俄国东正教堂,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俄军进行报复,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首当其冲。1902年,俄国东正教堂重建,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大部分被划入其界内,也是后来的苏联使馆。这两个府邸原先是由一座府邸分割之后而形成的,所处地段在东直门北小街以东的针线胡同,旧时也俗称“双旗杆”,大概是因王府里插立的祭祖神杆十分醒目而得名。从古今地图上判断,履亲王府就应在今俄罗斯使馆的地界上。出于好奇,几年前我有机会登上使馆西侧一幢正在施工中的楼房顶,居然看到了隐秘在馆内绿树丛中的几座绿色琉璃瓦顶大殿。要知道,如今任何文献也找不到履亲王府现有遗存的说法,文物部门也从未提及该王府的下落。以前受地理位置所限,人们无法看到或想到这座府邸尚有遗存,即使看见或许也未曾多想。通过长焦镜头,我清楚地看到大殿脊顶竟佩用了飞鸽形吻兽,这在我见到的所有王府中应是独此一例。当时这一意外的发现让我当时激动了好一阵,才将手中的相机持稳。这几座遗存殿堂看上去还较新,估计整修的时间不会太久,至于是否受维修时(可能在文革期间)的建材所限,还是完全依照原样使用这种飞鸽吻兽,答案只得留给今后了。
3.定亲王府遗留的完整院落
有关文献记载,在今缸瓦市以东至西皇城根之间历史上曾先后有两座礼亲王府,而且出现过第三代礼亲王(巽亲王)府和第四代礼亲王(康亲王)府在短时间并存现象。何故礼王府被一分为二?经请教冯其利先生后得知,所谓两座礼王府其实原来都是一座府邸分别由礼王家族的两支居住。代善七子巽亲王满达海这支住西院;代善八子祜塞之子康郡王杰书这支居东院。巽亲王满达海在康熙十六年(1677)获罪,使这支由此衰微。至其曾孙镇国公星海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缘事革爵,巽亲王府由内务府收回而闲置,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才赐予第二代定亲王绵恩为府。礼亲王则由杰书这支承袭,改号为康亲王。定亲王府作为老巽亲王府,东面紧靠礼王府;南邻羊皮市胡同;北到颁赏胡同;西面就是西四南大街砂锅居饭庄南北两侧,占地四十多亩。现今的书籍资料只提到今九三学社院内的古建为该府遗存。一天下午,我到此踏查,发现除了几间旧房和一颗几乎枯死的古枣树外,府北面只剩一段府墙。想到原府的西侧地段还有一大片没有看,想看看究竟还有没有遗存。当转到西侧大街,看见路旁有一座中西式门楼,上楣刻着“义达里”字样,就往里走,只见是一片样式相同的民国时代的旧式居所。靠南边的一条窄巷路北有两座结构完全相同的小四合院,估计建造年代也应在民国时期。窄巷的南面是一道高墙,里面是部队某部的招待所;巷子的东头被堵死,但欠起脚儿从墙的上方望去却能看见里面有一棵老银杏树和精致高挑的老房脊,看得出里面应是一所老宅院。我感到有些惊喜,就立刻从义达里出来,想再绕到哪个部队招待所里看个究竟,但当看到门口有战士把门时就犯了嘀咕,没敢硬闯,心想以后再说吧。我所踏查的这一地段从前都属定亲王府地界,勉强看到的那棵古树和老房脊却给我留下了悬念。
大约是在相隔近两年的一个初冬晴朗的早晨,户外寒冷并刮着大风,我再次来到那个部队招待所。当时看到进出大门的人很多,好像也有外地来京的游客,我于是就大着胆子往里走。还好,把门的战士可能把我当成了住店的旅客,没理我的茬儿。按照大致的方位,我找了一座藏在招待所北楼后面的一个带筒子瓦顶的破旧老房,从房子的举架结构判断,这应是王府的原建筑,像是个过厅。退后几步仰头向上望,一眼就看到过厅背后的那棵老银杏树繁密的枝头,我立刻来了兴致。这个过厅从前是进入内宅的通道,现已被用作了厨房,它的西侧有一个不起眼的门,要进去须按门铃。我犯了犹豫,但看见南侧楼上有几排朝北的窗户,何不上楼去看看?我就马上爬到了楼的三层。在楼道最北端的一个大会议间里,摆着几个乒乓球台,几名工作人员正兴致勃勃地打着球。我没打招呼就径直走到北窗前向下看,顿时惊喜异常!原来窗子下面竟是一座带垂花门的完整四合院,高大宏阔的宅院非同一般。这一突然的发现令我冲动,我掏出相机,不顾一切地打开紧闭的窗子,就冲着院子就照,冷气立刻顺着窗子就往屋子里灌。打球的人们感到了逼人的寒气,都回过头惊异地看着我。不知我在干什么,又见我是陌生人,一个样子有些严厉的人就过来质问我。我赶忙表示歉意并说就想拍下面的四合院。他冲我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四合院?下面是首长的住宅你知不知道?你拍照是何意?”我有些不知所措,一再解释说没别的目的,以前来过这,知道这个院子,就想留张好四合院的照片。他问我是谁叫我进来的,我就编了谎话,说我就住这儿的招待所。他又问我的单位,我连忙掏出工作证给他看。想赶紧了事,我马上关上窗子,然后对他说:“实在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说着就往外走。他虽未阻拦,却一了脸狐疑地看着我走出去……。
下了楼我才松了一口气,不自觉地又回到了那个过厅前,站了好一阵。一个送信的人敲开了那个院门,我不禁凑了上去。待送信人从院里去出来,就恳求开门的战士,说明来意。战士将我打量一番,不好拒绝,叫我等一下,就转身后回去了。不一会,他出来告诉我说:“首长的女儿同意你进去看看,但你看一会儿就走,别给我找麻烦”,我掩饰不住激动,走进院子我连声向那位首长女儿和战士道谢。我冲女士说:“您住的这儿以前是定王府的房子”,她有些疑惑地回答说:“王府到不知道,只知道这儿以前是普恩寺”。我听了后觉得很新鲜,自问道:“怎么又是寺庙了”?顾不上多说,我首先看到了前院这颗银杏树身上钉着带“A"字的红牌,说明树龄至少在三百年以上。树旁有一处叠石堆成的假山,靠门口的墙根下还弃置了一堆奇特的太湖石,一看就知是老宅的旧物,却不知原先装点在哪里。穿过精致优雅的垂花门,里面是一个敞亮的院落,正房五开间带筒子瓦顶,虽然主配房外原有的檐廊都被玻璃窗封住,但这样整齐的院子不失为现存四合院中的上品。我大致看了看院子的四周,没见到其他人,只有那位女士在院里忙活。拍了几张照片后,感到十分满足,不敢久留,我就再次向主人道了谢,随即离开了院子。
没想到刚走到招待所的院子,就撞见刚才在楼上质问过我的那个人。他一见到我,板着脸问我刚才上哪去了,为了不使他怀疑,我就把刚才的经过简单告诉了他,并强调说:“人家挺好的,没什么不愿意”。他听了后对我说:“你不是说你在这住吗?我刚查了住房登记卡,根本没你的名字,你到底要干什么?”不容我再多说,他就叫我跟他走一趟。我心想:我又没做什么歹事,能把我怎样?于是就跟着他来到了另一座楼里的一个办公室。他把我交给另一个管保卫的人,那个人上来就先核实我的身份,然后不容我多辩解,就给管片的民警打电话,报告警情。不一会儿,来了两位民警,问明情况后就将我带上车,一起开到了西单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里,民警同志向我了解事情的经过,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和拍照的动机,并问我为何当时不讲实话等等,我都一一如实回答,他边听边做着记录。听我回答完后,他让我坐那儿稍等一会儿,然后拿起电话就给市局作了汇报。我当时心里嘀咕:这事儿麻烦了。没想到他又问我的手机和单位的电话号码,随即拨通了我的办公室。只听见他对着话机说:“请问您是xxx单位吗?……..xx先生现在在吗?……您能告我他手机号码?……噢,好,谢谢!”核实完我的工作单位后,他郑重地告诉我说:“你不应该没经过允许就擅自到人家单位里去拍照,而且是领导同志的住宅……人家问到你时,你也应该实说…….鉴于你是头一次出这种事和你的态度,我们对你予以警告……现决定让你回去,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但你必须把拍过的胶卷交给我们。”他一边说,我一边点头,当听到要我把胶卷交出来,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底,虽极不情愿,但只得从命。
回来的路上,我感到十分的懊丧,心想怎么就偏偏又撞见那个人呢?如此倒霉!害得我还去了趟派出所,受了惊不说还被没收了胶卷,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但又一想,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吧。好在我又发现了定王府还存有一个完整院落,那个院落隐藏得如此深邃,若不努力探究,怎会搞清楚。回想起那院子主人和蔼的态度,又多少感到一些慰藉。我断定那个院就是原定王府的遗存有充分根据:首先那个院子是未经改动的旧宅院,且正好处在原定王府地界上,前面的那个过厅应是连接前后院落的过渡建筑;另外,那前院里堆弃的太湖石应是王府其它院子的旧物;再有,我注意到院的正房没有耳房,且东西配房往里缩进一块儿,留出来的空当在原先应有一条廊子从配房一侧穿过耳房位置进入后院,或作为与其它院落衔接的部位。这些迹象表明那个院落不是一个孤院,但尚能存此一完整院落至少也能为定王府增添不少谈资。后来我查看了明代的京城地图,那位女士说的“普恩寺”正好标在和她家宅院相当的位置。想来也怪,她怎么知道年代较远的普恩寺却不知曾赫赫有名的定王府呢?其实,宅院和寺庙在外形上也有明显的区别。唯一可以证明与寺庙有关的就是那棵古树,从挂牌起就至少三百年,在上推几十年就够着明代了,很可能是当初建府时特意圈留下来的。总之,这个不小的发现让我后来和他人谈起时总是津津乐道。
在我勘察王府的初期,由于初来乍到,手头缺乏信息和资料,又没能结识一些这方面的专家和知情人士,结果使自己对王府的了解相当有限,踏查的范围也主要集中于在各级文物部门中在册的属于文保单位的那些王府,而对其它“不在册”且大都残缺不全的王府(大都是贝勒府级以下的)却根本不知,甚至有的在胡同里见到了还以为是大宅而没拍照,后来醒过闷儿时宅邸已被拆除,以致后悔莫及!
4.东交民巷里的的神秘建筑
东交民巷是北京的一条最长的胡同,却经历了百余年的沧桑。巷子内沿街散布着的各种西洋式建筑,见证了近代中华民族蒙受耻辱和帝国主义列强贪婪掠夺的历史。在我的印象里,这一带除了旧时的西洋建筑就是解放后修建的政府办公大楼。就在这条街的东段路口把角处,有一座造型别致、小巧玲珑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堂顶有两个高耸的锥形尖塔。堂的正面上方站立着一尊洁白带羽翅的圣弥厄尔雕像,耀眼夺目。由于教堂前院进深很短,且有杂物遮挡,在教堂前拍了几次,照片仍不甚理想。经过一番周折联系之后,我得以在某日登上离教堂不远处的首都宾馆大楼顶俯拍教堂的全景。记得当时我是和另外一个伙伴一起上的楼,除了教堂外,原比利时使馆内的紫墙绿顶式洋建筑群也相当诱人,我俩一通拍个尽兴。就在我们正顺着大楼最高处的圆塔顶端外的铁梯往下撤离时,我看见下面巷子路北的楼群中有一座“奇特”的青灰色中西合璧式院落,和四周的建筑相比显得有些破旧,房顶都是中式灰瓦铺就。出于一种直觉,我当即就冲着那里拍了一张。由于当时已感到有些累,且要急于下楼,并没有换上更合适的镜头。
后来在翻阅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时,发现那个“奇特”的中西式“四围院落”正好处在当时的辅国公盛昌府界内。由于兴奋和好奇,我又去了东交民巷。在那里,我大致判断了一下“奇特院落”所处的位置,发现就在它前面的街上仍保留着一座造型别致的老式法国邮局。在那座院落东边不远有一座带西洋式大门的大院,有武警战士守卫,门外两旁立着一对旧石狮(原府的旧物),能瞥见门里花坛前有一排太湖石。经查阅《北京东城文物建筑》图册和英文版画册《The Boxer》(中文译名为《义和拳》)等相关资料,并请教冯其利和刘阳后得知,那一地段清代时是一座公府,乾隆京城图上标注的是辅国公盛昌府,在近代曾是法国使馆。据记载,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随后法军抢占了著名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府(在辅国公盛昌府西北侧比邻),声言要“租借”作其使馆。如此显赫的王府,事关大清的脸面,经反复交涉,法方才同意另以纯公府作为其使馆。当清廷将纯公府拱手交给法国人时,这个末代公府的主人纯堪(辅国公盛昌的后人)正奉命在遵化守护东陵。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还拍了一张照片,虽然拍得场面较大,光线也不理想,但由于是俯拍,经剪裁后仍能从照片上看出院子的全貌。从照片上看,那个院落的正面和门采用西洋式装点,院子的北房面阔较大(大概有五间),前出抱厦,屋顶是筒子瓦铺成,属中式做法且规格较高。院子的其他房屋都是合瓦顶,西配房屋顶与北房一侧屋顶平缓连接。院子东侧与西侧不对称,但也是合瓦顶房屋。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有机会走进那埋藏着“奇特院落”的某机关宿舍院,得以靠近仔细观看。从整体看,那座院落像是在原中式房屋基础上改建的,前屋墙缝上留有明显的“带刀灰”痕迹,属民国后的做法。由于后面带抱厦的大北房的檐廊已被封住留作居住空间,外墙也已改换成新式墙面,除了房的后檐角尚能看出一点儿旧式砖雕装饰,无法进一步看到早期中式建筑的细节;院落正立面的墙垛上镶嵌着精细的中式砖雕,门的上端女儿墙呈尖形,也雕有精细的花纹图案。我当时询问了几位在场的住户,他们大都不知其来历,但有一位住户说此建筑曾是日本使馆,这一说法倒让我疑惑很久。因为按老地图所标,原日本使馆应位于现北京市委地界内,而原法国使馆正好涵盖了这一地段,而那座带抱厦的大北房距东边带石狮子的院子(应是原纯公府的主院)仅一墙之隔,很可能是原公府跨院或花园中的遗留之物,后经巧妙改建才形成目前这种“奇特”的中西合璧式院落。但这个院落的来历究竟如何?我至今尚无准确的答案。
5.历睹卓公府的消亡
对孟端胡同45号卓公府的考查从2002年3月初开始,直至2004年12月初整个宅邸被彻底拆除为止历时近三年。初次到访,尚不知这里还有一座“卓公府”。只见笔直幽深的胡同两边尽是青砖灰瓦的老宅门,一幅典型老北京胡同的景象。在胡同西头路北有一处坐北朝南的老宅,门牌为45号,门楼高大,宅门东侧的部分倒座房改成了车库。顺着宅子东侧的夹道,可通往后面的小盆胡同,宅子的后墙也刚好砌在了小盆胡同南端。此宅纵深整跨前后两条胡同,足有80米深。从夹道侧墙抬头仰望,在浓密的树枝间隐露出几座线条流畅的宽大屋顶,透着几许神秘。宅的西侧还有一个大跨院(属同一门牌号),进深比东院略短,后部延伸到了大盆胡同,一道紧闭的大铁门横在正门口,使人无法看见院子里面。大约半年多过后,我看到了中央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发的一份《清末王公府第地址单》,这样记载:奉恩辅国公载卓,阜成门内锦什坊街孟端胡同,共房八十间。真属巧合,那里也有王府!我马上就想起当时在胡同里寻摸过的45号大宅,那里面再没有哪个宅院能与之相匹,可以肯定45号院就是卓公邸。第二天我就驱车赶往那里,令我吃惊的是45号院的墙上竟赫然涂上了“拆”字。再向胡同南面望去,以前那片曲折幽深的胡同已成为一片破碎的砖瓦残垣,地上裸露着几棵古树,不远处的工地上矗立着几座正在施工的楼宇和塔吊,能听到隐隐传来的机器的轰鸣声。这幅景象明白地告诉了我:这个院子已被判了“死刑”,金融街正紧锣密鼓地扩张。围着那院子又转了一圈,东西两院所有的门依然紧闭。向胡同里的住户打听,都说45号院正在交涉之中,里面有的住户不愿搬走,也有的不同意搬迁的补偿条件。看到一辆轿车停在院前,下来一个中年男子开门进了院子。我走到门前,按了几下门铃,里面的人隔着门问是谁?干什么?,我冲里面说:“就想看看院子,这么好的院子要拆了很可惜,拍几张照片留下”。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这是机关宿舍,没有约请不能进来,好多人都想照相,我们都没让进”。无奈之下,只好打道回府。
再一次来孟端胡同大约在2002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先沿着院子东边的小巷往后走,猛然间我发现最后一进院已被拆掉,第三进院的正房已暴露在废墟之中,后檐下的彩绘和房脊上精致的砖雕清晰可见。环顾周围,已看不到宅后的两条胡同了。后面不远处有一条横向大道的路基已经挖就,阻断了往北去的道路。真想不到变化如此之快!我看四下里好像没人看管,掏出相机对着正房照了几张,感觉不理想,只算留个资料。我心里有点儿犯急,心想再不拍,哪天拆了可就瞎了。宅的东面有一座四层楼,以前是一座学校,此时已经腾空,此片的拆迁办就驻扎在楼里。要俯拍宅子全景,只能上楼顶,但绝不能跟他们打招呼,否则根本没戏。看到楼门口的人走开后,我就悄悄往楼里走,还好没遇见人阻拦。我直奔到四楼,没发现有去楼顶的通道,我心里有点儿凉,忽然又看见楼道另一端有一小截楼梯能通到四层半的一个小屋,我预感到有点儿指望。进去一看原来是个水房,屋顶上还真有一个不足二尺见方的天窗。我从四层教室搬来一张课桌,踩上去用力推开天窗盖板,先将摄影包送上房顶,然后双手摽住天窗框使身体上引,再用胳膊肘使劲撑住上沿,将身子一截一截地送上了房顶。抑制不住兴奋,我急忙走到靠近院子的顶沿,只见45号院尽收眼底,院子里浓密的枝叶已变得稀疏,静谧的殿堂像一座座完好工艺品从树丛中显露出来,淡淡的阳光映得院子一片昏黄,能将这种美景收入镜头足能让我终生无憾。爬上来时蹭了一身的尘垢,但出于兴奋也顾不得这些,我更在乎这次机会,心里不禁感叹:再过几年恐怕也没力气这样上房了啊!再说那时即使能上也没得可拍了。忙活完了之后,我不肯马上离去,面对脚下即将被高楼而取代的院子驻足端详,一种无法形容的思绪在脑海里回荡了许久。
后来在朋友的协助下,我有机会走进了45号东、西两座院子。头次来东院,走进大门楼就能看见正对着门楼的精美厚实的垂花门,院子两侧不是通常头进院落的格局,而是各有一座配房,使这个宽绰的院子不显空旷。但这两个内外门楼和宅院都处在一条中轴线上,倒让我觉得新鲜。这既违背了旧时宅邸格局也不符合公府(镇、辅国公府)的定制。我猜想这很可能是在民国初,王府后人变卖府邸之后,后来的主人怕树大招风而改动了格局。最有可能改动的就是临街的大门,因为现在的门楼就属从前很普通的如意们,跟这样宏阔的宅邸绝不相配。那座垂花门做得如此气派是我所见之精品,它外侧两边的山墙上镶有精致简约的砖雕图案,线条细腻如刀刻,磨砖对缝的青砖墙面未经任何人为粉饰,令视觉爽快。内院只剩下第二、三进院子了,最后一进已拆掉。第二进院子里广植着各种花木,把内院遮盖得幽暗清凉。垂花门内两侧的绿色抄手游廊与整个主配房的檐廊相贯通,构成完整紧凑的院落,使人有一种浓厚的归属感。所有房屋建在高出地面的青石台阶之上,檐廊上仍遗留着旧时的彩绘,廊柱上下分别佩有雀替和须弥座,使这座未经拆改的宅院面貌非凡。院子的每个角落都有主人栽种的植物,有丁香、竹子、松柏、海棠、柿子等等,颇具匠心。听住户讲,每到春季,繁花盛开,香溢满院,走到胡同里都能闻到,还有许多种候鸟也会按时落此栖息。最吸引我的还是垂花门旁的一棵“歪把子”丁香树,底干有脸盆口粗,几棵碗口粗的枝干向不同方向伸展,繁茂的枝叶遮掩住游廊和配房的一隅,姿态生动,是我所见到的一棵最奇特的丁香树。第三进院与前院不通,得从东侧夹道的侧门进去。此院面积和第二进院相当,正房前栽种着一片竹林,在微风中不时沙沙作响,使这个人气不旺的院落显得出奇的寂静,倒像是一处隐僧的归所。我不由得想象这所大宅在雨雪天里会是何种景象,那只有住在里面的人能有幸饱赏了。其实在昔日的京城,许多美不胜收的景致就隐匿在胡同的宅院中,数量远非区区可数的苏州园林所能匹拟,人们不必常常走很远去逛皇家公园,眼前的美景就叫街坊四邻消受不尽。
45号的西院以前住着一位部队首长,现已去世,只剩家属。2003年10月的一天下午,由北京民间保护胡同四合院的先锋华新民女士(法籍,祖父为著名华裔实业家;父亲为著名建筑师)牵线,我和她一起来到45号西院,拜见了已故首长的两个女儿并一起观看了院子。这处院子紧邻东院,当时有前后三座房屋,均为五开间,没有配房,最后一进院的进深较窄。院子虽不呈四合的格局,属于原府邸的跨院部分,但规格绝对够得上公府级别。言谈间,她们倒是对这院子的来历很感兴趣,也表示拆了太可惜。她们家是七十年代后期般到这里的,小女儿仍对以前的环境记忆犹新,她说:“以前这一带成片的胡同,安静极了,夏天胡同里特别阴凉,而且交通也方便,我们从家去西单,走着穿两条胡同就到。我父亲退休在家时每天傍晚都顺着胡同散步,有时看看胡同里的人下棋,还掺和着一块玩”。她也听人讲,从前这个宅子特别大,从宅的东头一直到西边顺城街的城墙根下,有好几个门牌号,胡同南边也有房。我最关心的是此院的命运,就问她们这院子到底拆不拆。大女儿没直接回答我,只说:“这院子是公房,我们也不知道上面管理部门跟开发商是怎么谈的,也只好在等。”华新民告诉说,这45号院一年多以前是被文物主管部门确定为北京保留的539个四合院中的一个,前些日子一些专家和政协委员还去东院看过,都说很少见过这样好的院子。她还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这座院子。
就在我去过孟端胡同45号西院之后不到一年,也就是2004年7月的一天,我看到《京华时报》刊登着:“孟端胡同45号院部分被拆”的黑色大标题,小标题写着:“该四合院被专家认为是北京四合院中的上上品”粗略扫读了一遍文章后,我迫不及待地驱车赶往孟端胡同。这次跟以前不同了,胡同两边都成了工地,胡同西口还有保安把守。没法从正面进去,我就将车停到了后面的武定胡同,穿过新修的大道,从工地外铁皮挡板的缝隙间看到一辆推土机正在隆隆地作业,除了两道山墙和一片废木瓦砾外,45号西院已拆得看不出模样,院址旁边已挖成了一个大地基坑。我心想来晚了,再也看不到了西院了,心情十分郁闷。再看东院的另一侧,也挖出了一个大土坑,东院俨然成了一座孤岛,浓密的树叶上落满了尘土,显得毫无生气,等待她的还能有什么哪?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每次从武定胡同前的大道上经过,我总不由得要望一眼45号东院,看到她孤零零苟延残喘了这么长时间,不由得又心存一丝希望。据华新民女士讲,她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将45号院保留下来,做成一个高品级的饭庄、茶室或俱乐部,这在日后高楼林立的金融街里,有这样一处古典庭院作为歇息场所也不失为让各方都皆大欢喜之为。不知她的倡议是否已被有关部门采纳,或者是正在运作着某个具体方案而拖了这样长时间。再一想上次去45号东院比较匆忙,拍的片子不理想,就惦记着过几天再进去补拍几张。
我的拍摄笔记上记录的日期是2004年11月29日,这是久违了之后,我与孟端胡同再次相会。但见先前这条笔直幽长的胡同已被截去大半,剩下的西半段已被包围在喧闹的工地中,变成了一条往来的道路,机器的轰鸣声直逼入耳。我不由得回想起两年前头一次来此的情景,同样是初冬的午后,浅淡的阳光映照在青砖灰瓦上,宁静而安详。而如今,除了45号东院和两座残缺不堪的旧宅外,尽是废弃的砖瓦土堆和临时性民工住房。这里已基本上看不到原来的住户,只有几个商贩摆着地摊,向过往的民工出售日用品。令我意外的是45号后院的侧门竟敞开着无人把守,进去一看,原住户都已搬走,院子之间的隔断已被打通。从后院到前院显得空空荡荡,地上落满了树叶,垂花门正面的屏扇已撤走,前院房子里尽是丢弃的家具、用品和残留的木隔断。这幅败落的景象,让我十分扫兴,原先的拍摄欲望也随之消退。但又一想,这院子尚命运未卜,就当拍些资料留着也好,于是我就满院子找角度拍了一溜够。拍到第三进院正房时,我看见正房屋内有几个人在忙活,还亮着灯。我立刻有点儿紧张,心想这些人肯定有来头。这时正好从门外又进去两个人,并没理会我的举动。我直纳闷:凭经验,在这样的场合下,一个陌生人拍照总是要被追问的,他们竟然不理我的碴儿?该拍的也拍了,怕再惹出麻烦,我随即离开了院子。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中午华新民女士打来电话,伤心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他们昨晚11点钟开始拆45号院了,一直就没停,现在还在拆哪…….”。这一消息令我十分震惊!虽然早就料到,但觉得太突然。心想昨天下午那里还风平浪静,怎么当夜就搞起偷袭?我想看个究竟,就立刻驱车前往孟端胡同。刚驶进老顺城街口,就看见工地入口站着几个保安。其中一个见我驶来,打出了停止的手势,并示意我赶紧离开。没辙,只好掉头开到后面的武定胡同去。站在一个土坡上,我望见45号后房上部分瓦片已掀去,暂时还看不到有人在拆房。我没想久留,就又回单位去了。我其实就想看那些人是怎么拆院子的,因此不肯就此罢休。下午再去,我没直接从中午的入口进去,而是绕到别处和民工一起先混进旁边的工地,再辗转来到45号院前。出我意料的是,整个院子都已被铁皮挡板围住了,使人无法靠近院子。尽管如此也遮掩不住拆房的举动,只见门楼上有三个民工在掀房上的瓦片,还有一个正挥镐用力地刨起门楼上沿一侧的博风砖。他们一见我举起相机,就把头调转过去,有的干脆缩回进院子。为了看清院子里面成啥样子,我蹬梯爬到院子对面给民工搭起的临时住房的三层楼上
,从一间臭气难闻的房间的后窗口,我看到原先那座漂亮的垂花门已被拆走,两道墙之间留下了一个大豁口,里院的配房顶也已挑开了一个大洞。见此情形,我的心彻底凉了!失去垂花门的院子就如同没了头的躯干将被一刀一刀地被割去,我深知这院子已不可救药。在院子东侧挡板外,有几名媒体记者也在观看。听其中一位老兄讲,这个院子将迁建到阜城门历代帝王庙东侧,负责拆除的是文物部门下属的工程队,拆下的房屋构件将统一编号待复建时再用。我问他这个院子为什么没留住,他听说是这里要开一条路,这院子正好骑在规划中的道路上。我听后觉得荒唐滑稽,心想迁建还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给有关人士一个交代罢了。我不由得想起我曾经踏查过的迁建后的两座王府:一个是1994年从现在全国政协办公大楼位置上迁到朝阳公园内的顺承郡王府;另一个是1986年从现在宽街中医医院大楼位置上迁建到密云郊野公园内的大公主府。当时看到复建后的工艺和原先的简直天壤之别,光看墙面就不是“磨砖对缝”,很粗糙,而且府的格局也有改变,还另添新物。这样的迁建从建筑、样式到整个的味道,都不会是原来的了。第二天我看到《新京报》上这样写着:“…..随着这个院子的开拆,以明代画家王孟端命名的孟端胡同这个地名也将消失……”.我看后不禁感慨:是啊,不仅这条著名的胡同消失了,而且代表着京城建筑文化和王府文化的这座典型的公府,拆一座就会少一座,想要再现昔日的面貌是不可能了。